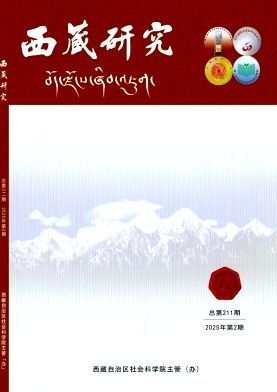| 295 | 0 | 22 |
| 下载次数 | 被引频次 | 阅读次数 |
18世纪始,关公先后以武圣关帝与藏传佛教护法神“真仁杰布”等身份深入蒙藏地区,与当地岭·格萨尔信仰交汇。关公与格萨尔王分别为汉、藏文化圈中的战神,二者神格职能相近,相关文学、图像叙事也被相互比附,以致蒙藏地区广泛出现了将关公称作格萨尔、关帝庙称作格萨尔拉康的文化现象。“白面关公”唐卡应是关公信仰深入蒙藏地区后,与格萨尔信仰融合而成的视觉化呈现,体现出关公信仰在清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突出意义。
Abstract:From the 18th century onwards,Guan Gong penetrated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regions in the roles of Martial Sage Guan Di and the Tibetan Buddhist Dharma protector "Drinrin Gyalpo"(Wylie:sprin ring rgyal po) among others,converging with the local Ling Gesar belief.Guan Gong and King Gesar are war deities i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 respectively,with similar divine functions and comparable literary and visual narratives.This led to the widespread cultural phenomenon in Mongolian and Tibetan regions of referring to Guan Gong as Gesar and Guan Di temples as Gesar Lhakhangs.The "White-faced Guan Gong" thangka appears to be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fusion of Guan Gong belief with Gesar belief after Guan Gong worship penetrated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regions.This reflects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Guan Gong belief in the multi-ethnic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孙涛:《一件清代护法将军唐卡考》,《收藏家》2021年第4期,第104页。
(1)图片来源于鲁宾艺术博物馆官网。
(2)参见孙涛:《一件清代护法将军唐卡考》,第100页。
(3)图片来源于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站,编号:88591。
(4)参见许志平:《中国佛教寺庙宝藏——散华聚念》,中国台北:藏新艺术有限公司,2014年,第47页。
(1)该幅唐卡见于2014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参见许志平:《中国佛教寺庙宝藏——散华聚念》,第45页。
(2)孙涛曾尝试为鲁宾艺术博物馆所藏唐卡定名作出一些合理化解释,但他也提出疑问:“就此幅唐卡的主尊形象而言,明显与关公形象有着极大差别。”参见孙涛:《一件清代护法将军唐卡考》,第104页。
(3)另有三世章嘉《供养关圣帝君赞颂文》《供养关圣帝君护法祈请文》之原文与译文,亦可参考。参见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80—81页;王帅:《藏传佛教关公信仰新论》,《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第102—103页。
(1)三世土观称关公与密宗神祇卫则姊妹护法(■;又称红命主,■)、尚论多杰东都(■)、赤尊赞(■)等为“同一心识”,从而将其正式改造为藏传佛教神祇。参见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第82—83页。
(2)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文集》■函,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藏本,转引自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第84页。
(3)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第85页。
(4)参见加央平措:《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第33页。
(5)二世嘉木样著有《汉地声名遍知大战神真让嘉波关老爷之祈供法》;察哈尔格西著有《护教大帝关老爷之祈供法·心愿普赐》《统辖中国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召引所欲之铁钩》《关老爷之煨桑文》。参见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第85—87页。
(6)参见Fitz Herbert,S,"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Revue d'Etudes Tibetaines,2020,p.220.
(1)参见Fitz Herbert,S,"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229.
(2)参见董晓荣、齐玉花:《<东方支那战神关帝爷前供神饮法·招随愿之钩>之内容探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84页。
(3)该幅唐卡系雍和宫收藏。雍和宫中仍收藏有多幅“关公”唐卡,每幅唐卡除上方密宗神祇有改变外,其主尊形象、眷属配置均与本文所举图6相近。参见雍和宫编:《雍和宫唐喀瑰宝》,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
(4)该幅唐卡系“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人物形象、风格特征等与雍和宫藏关公唐卡极为相近,应为“北京地区唐卡作坊之作品,且很可能与雍和宫有关”。参见钟子寅:《关老爷游蒙藏——从院藏双幅关公唐卡谈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故宫文物院刊》2019年第4期,第64页。
(1)参见罗文华:《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绘画研究》,《故宫学刊》2004年第1期,第344页。
(2)图片来源于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站,编号:50010。
(1)朱一玄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59页。
(2)有学者认为,章嘉创作《关老爷之祈供法》大概是在1748—175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关公崇拜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不晚于1707年。参见加央平措:《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第28页;胡超:《佑顺寺关公殿:藏传佛教最早的关公崇拜探源》,《中国藏学》2023年第3期,第150页。
(3)海西希、李福清及国内众多学者已关注到关公与格萨尔在相关文学叙事中的关联性,对二者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梳理。参见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54—377页;陈岗龙:《内格斯尔而外关公——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第56—60页。
(4)参见董晓荣:《从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插图看蒙古族关公信仰》,《藏学学刊》2018年第1期,第80、84页。
(5)国内外学界对《汉区佛教源流记》的成书时间仍有争议:有1736年之说;有18世纪中后期之说。菲茨赫伯特在此是基于1736年一说进行论述的。
(1)菲茨赫伯特认为,这里与关公相联系的“格萨尔王”和日后流行于蒙藏地区、与关公信仰发生混淆的“岭·格萨尔”不是同一人,前者是7—9世纪西藏北部的一位(世俗)部落头人,而后者是英雄史诗文学中的“战神”,但他在此处并未说明得出该结论的参考材料。笔者认为,此时出现将“格萨尔王”与关公相联系的叙述线索仍值得重视。《源流记》中所载内容如下:“关老爷是汉区政教之护法总神……此神刚正不阿,办事极有分寸,后来跟随文成公主进藏,即所谓山寨先巴和格萨尔王者,皆为彼矣。另有(关老爷)和拍格孜药刹,二者天性皆然一致指传说故事”(注:此处“山寨先巴”、“拍格孜药刹”分别为赤尊赞、卫则姊妹护法的音译名称)。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197;贡布嘉:《汉区佛教源流记》,罗桑旦增译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8—59页。
(2)此处“跨区域网络”指由清初“绿营兵”发展而来的,囊括满、汉、蒙等多民族士兵的驻边军队。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p.191、198.
(3)参见董晓荣:《从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插图看蒙古族关公信仰》,第82页。
(4)该书认为,格萨尔化的关帝塑像与被称作格萨尔拉康的关帝庙早在18世纪已经形成,拉萨的关帝庙在兴建之时已有格萨尔拉康的称谓,殿内的关帝像在塑造之始就被藏族群众称作“格萨尔王”。参见加央平措:《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第12—16页。
(5)参见加央平措:《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第38—40页。
(1)这位蒙古上师的身份尚未确认。据菲茨赫伯特介绍,该活佛世系与清朝在蒙古乌里雅苏台(Uliastai)的行政区划关联密切;《蒙古的宗教》中将这位宗教上师称为“长胜呼图克图睿班智达敦珠多吉(1820—1882)"。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238;海西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37页。
(2)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p.237-241、244.
(3)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p.244-245.
(4)格萨尔的(战神)骑乘形态称“格萨尔·诺布札杜”,是绘画作品中最常见的格萨尔形象。
(1)图片来源于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站,编号:4248。
(2)图片来源于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站,编号:60615。
(3)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p.235-236.
(4)海西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第136页。
(1)参见Fitz Herbert,"The Geluk Gesar:Guandi,the Chinese God of War,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p.234.
(2)白梵天、念钦唐古拉山神与姊妹护法之间均存在一定联系。参见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4、117—118、144、148、167、169页。
(3)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谢继胜译,第166—167、237—238页。
(4)该唐卡系四川博物院藏《格萨尔画传》系列唐卡之一,“念钦多杰巴瓦则”即念钦唐古拉山神。
(5)参见徐斌:《格萨尔史诗图像及其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第34页。
(1)参见包头市五当召管理处编:《五当召珍藏——唐卡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2)参见王家鹏:《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实——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第34页。
(3)参见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编著:《格萨尔唐卡研究:汉、藏、英》,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页。
(4)杰夫·瓦特:《藏族文化英雄——岭·格萨尔艺术和图像的初步调查》,张长虹译,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编著:《格萨尔唐卡研究:汉、藏、英》,第180页。
(1)该唐卡系蒙古佛教艺术中心收藏。参见钟子寅:《关老爷游蒙藏——从院藏双幅关公唐卡谈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第72页。
(2)参见包头市五当召管理处编:《五当召珍藏——唐卡壁画》,第214页。
(3)参见楼含松、王旸午及:《关公红面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32—142页。
(4)有学者认为,二郎神“三目”特征的出现、传播与大众接受存在一个“层累造成”的情况:“此神出现的时代很早,但他‘成为’三眼之神则甚晚,之后这一特征越来越常见,后来居上,反成民众心中此神最鲜明的形象特点。”笔者认为关公“红面”特征的出现、接受与此规律极为相近,即同样体现神灵形象变迁的层累性。参见李飞:《阙庭神目:二郎神三眼形象的流传与接受》,《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2期,第93页。
(1)钟子寅:《关老爷游蒙藏——从院藏双幅关公唐卡谈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第73页。
(2)该唐卡虽被定名为“格斯尔汗(Geser Khan)”,但能够辨识出主尊身侧二位侍从为周仓、关平,且该眷属配置与雍和宫藏关公唐卡极为相近,可以据此确认唐卡主尊实际应为关公。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J219;B933;K249;B946.6
引用信息:
[1]曾靖柔.“白面关公”:清代“关公”唐卡所见多民族信仰交融与形像再造[J].西藏研究,2024,No.207(04):60-75+160-161.
基金信息: